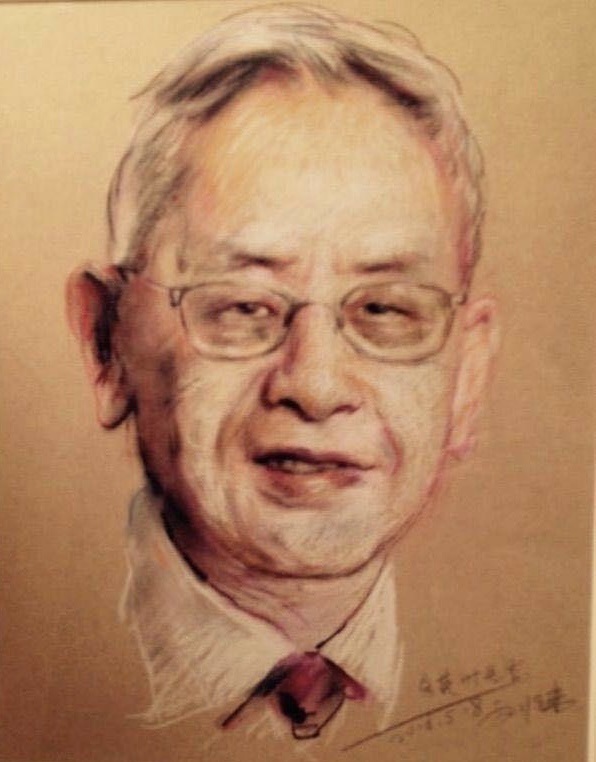一個人無法選擇降生方式,卻有可能選擇告別世界的方式。余英時先生離去得如此從容優雅,使我的悲痛化為仰慕。余先生與老友疑似話別的最後通話,幾個小時後的凌晨,前輩便在夢中圓寂。惟有臻達此等境界,才能淡定參透和穿越生死。
1990年初識余先生,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任訪問學者。那時有好些大陸文化人浮桴於海,都是在時代風暴折翅失群的驚鴻。他們陸續聚攏於普林斯頓大學,我也在其中。萬里飄萍擱淺於卡內基湖畔,纖弱根鬚探入陌生的土壤。那時我對將要開始的漫長異域生活毫無心理準備。如果沒有余英時,大學就不會有此研究項目。命運扁舟若非在此間繫纜,去國者將會更徬徨鬱卒,其後的流亡歲月極可能隨波逐流,甚至淪為靈魂無依的畸零者。
那段日子苦澀之中的清甘,來自余英時先生對流亡文化人的精神關懷。他在東亞系壯思堂給我們講中華思想道統的流變、講秦制、講儒學源流、講士的內心世界、講《紅樓夢》、講胡適和陳寅恪……我在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消磨時間最多,胡適正是前任館長。從胡適到余英時,自由思想被逐離神州,卻在另一片土地再生,思想燧石的傳承劃出了歷史弧度。
普林斯頓荏苒九年,儼然第二故鄉。其間種種軼事,我不欲重複自己寫過的文字,只想說幾段私人記憶——
除了初到普林斯頓曾被邀到余家見面認識,我和余先生幾無私人接觸。及至我逐水草而居,遷往首都華盛頓,只寫信告知前輩,並無登門辞行。再訪余府,竟隔了多年,其時余英時已榮休。我這詩詞後學素仰先生舊體詩功力深厚,便冒昧將拙作寄給先生。孰料很快收到回信,字裡行間儼然詩友間的平等討論,還附有他的幾首手書七絕。
重登余府誠因詩緣,卻不止於此。余先生和陳淑平兩位前輩待人親和真誠,關心我和家人遷居大華府之後的生活、工作。其後我多次登門拜訪,話題海闊天空。余先生的學術殿堂,我無力窺探。本來汪精衛、陳寅恪的詩尚可一聊,但余先生“功夫在詩外”,他的《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》和《雙照樓詩詞稿》序文,都不是在談詩本身,而透過變幻莫測的歷史雲煙,探究作者的幽微心理和時代投影。我不敢說能讀懂余先生著作,至少這兩篇是讀懂了。
不過余先生說自己不是詩人,詩歌並非他的事業。好比他圍棋段位很高,曾贏過友人林海峰九段半目,又寫過多篇棋評,但圍棋並未進入他精神世界的殿台。余先生始終不願出版自己的詩集,亦緣於此。
回憶與前輩相對,多是說家常話人生。只有余先生能將家常話不著痕跡地聊出深意。老子所言的玄覽是一種化境,“心居玄冥之處而覽知萬物”。我和余先生談台灣之旅心得,感嘆民風人情之淳厚,這一脈在中土已湮淪的文明,卻在邊陲得以延續。余先生說:“台灣民眾沒有革命記憶,連辛亥革命的記憶都沒有。”
我又和前輩說起,來美幾十年清貧淡泊,對利誘已不為所動。但文人常耐不住寂寞,要刷存在感,容易在看似不虧大節的事情上犯迷糊。余先生淡然一笑,說存在感不是想要就有的,他就希望人們忘掉自己。我由此悟出,不甘寂寞是一種文人慾望,不求聞達是一種賢哲境界。
余先生書房有一副對聯“未成小隱聊中隱;卻恐他鄉勝故鄉”。這是余先生集蘇東坡和陸游之句所撰,由他的岳父、教育家陳雪屏手書的。此聯詮釋了余英時的鄉國觀和“存在感”。他警惕強加給他的國家符號,諸如國學大師、國之瑰寶之類。余先生堅持自己不從屬於任何國家,他的學問思想也不囿於某國。
余英時既拒絕“國家”印綬,更蔑視權力的籠絡。彼岸學界中人求見,寬慈德厚的余先生都以禮相待。但對與權力勾連甚至負有某種使命的來人,余先生凜然決絕。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(後因“違紀”被留黨察看)求見,先來電話:“我向組織匯報過,上面已經同意我來拜訪您。”此言一出,電話即被掛斷。帶着任務的安徽潛山鄉親團前來遊說,懇請余先生回鄉看看。得到的回答是“我沒有鄉愁。”
前輩不戀鄉土,“哪裡有自由,就是我的故鄉”。這種情懷深植於人性、人道、人本、普世價值。不知不覺,我已受到余先生“人之所至,根亦隨之”的影響,和前輩聊家常,漸少話及故國,而對眼前落地生根之地的榮枯有了更多感情投入。
余先生文風來自私塾根底,古文與白話文切換自如,典雅大氣,但他從不好為人師。余先生來函和贈我書法條幅,都用平輩稱呼。回憶和余英時交談,如果說前輩有過叮囑,那就是“過好自己的生活,做自己喜歡的事”。這話他對我說了好幾次,淺層理解是經濟要自立,方能人格獨立;深一層意思,人活得充實與否,是由自己所做之事來定義的。
我兩年多前退休。余先生和淑平師母特地請我到普林斯頓上海菜館“大千美食林”致賀——前輩將退休視為人生重要的進階,他恭喜我終能全心全意做自己喜歡的事了。
我有一次信口提到,將要去舊金山賀母親九十壽辰。從普林斯頓回來沒幾天,就收到余先生手書賀卡,要我代為祝壽。我母親只比余先生年長四歲而已,她收到賀卡,感動不已。今年春天,我岳父老音樂家孫慎以105歲高齡辭世,余先生和淑平師母寄來悼念卡。記得我曾對陳淑平前輩感慨道:余先生真有古人之風。師母正顏答道:“我們都是現代人,不是古人。”我猛省,余先生立世為人和治學著述的視界胸襟,並非都來自中華文化原生的價值。於我而言,西方文明的精髓,至今仍在補習。
余先生贈我《余英時回憶錄》,讀來彷彿聞到皖西大山氣息、私塾墨香、大時代轔轔戰車和瀰漫硝煙,更觸摸到歷史榫接處的年輕讀書人的心路。感觸之餘,我陸續寫了幾首詩,聊作讀書札記。其中《剖蚌篇》為:“駑馬馱經詡獲麟,百年難滌後前塵。西潮漲汐誰珠礫,舊服遺繩自寡均。遽報雲中邊角急,爾來隴右驛烽頻。陳胡曠士皆眠草,聒殺神鴉玉鼎新。”陳胡指陳獨秀、胡適。
這一首是有感於《余英時回憶錄》對共產主義流入中土的反思,先生認為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、“公”為善“私”為惡的儒家觀念,在晚清對外來思潮產生誤讀而牽手。我讀此章,生出一個文學比喻——批錯八字的盲婚。
余先生看了這組詩說:“好了,到此為止。”這組讀書札記我就再也沒往下寫。余先生不接受別人當面稱讚,我這組回憶錄讀後感呈給先生,有當面稱讚嫌疑,被先生阻止,在所當然。
記得某次我到訪,客廳牆角放著一副余先生畫像,淑平前輩說,這是大陸一位畫家憑照片畫的肖像畫,剛剛寄到。我覺得筆觸傳神,便用手機拍照。但後來多次拜訪余府,再沒有見過此畫。余先生不會懸掛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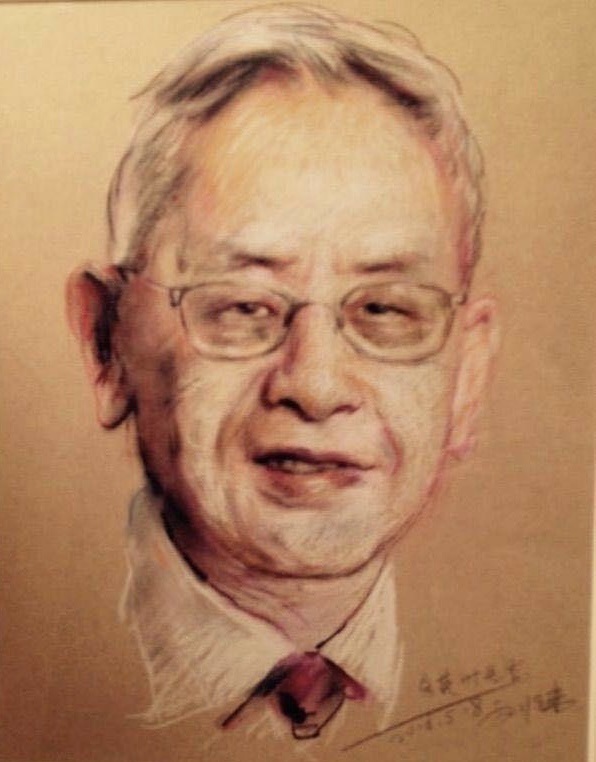
《余英時回憶錄》關於先生在香港新亞書院和美國哈佛的學術履痕,令我掩卷沉吟再三,卻不再以詩詠之。我問何時能看到回憶錄下卷?先生答:未必會寫。他還拿出提綱給我看,這些時間事件人物的列表來自台灣一學人(我忘記名字)對余英時的口述訪談整理。先生說,下卷就是這些內容,但他再次強調,很可能不會寫下去了。
我看了提綱不免感喟,當年這群去國文化人如驚弦唳雁,散入卡內基湖蓼花深處,普林斯頓儼然精神錨地,各人心史都有一個堅牢的記事繩結,就是余英時。他拯救的不是流亡者肉身,而是靈魂。然而先生回顧此生,完全沒把這當作值得記敘的事。余英時肩上承擔着更大的道義和事業,乃至回憶錄都得讓位於這一使命。
雖則余英時回憶錄已非個人敘事,這本身就是文化思想史重要一章。不過他已離我們而去。我母親聞知余英時夢中仙去,第一反應是:“他真好福氣。”老人家對生死的感悟自是不同。
余先生殮葬之事,外界無人知曉。淑平師母和女兒料理好一切,才向余英時的至交好友通報。這是先生家風,自己之事絕不麻煩別人。於是想起某次我到訪,聽得余府的煙火預警器間歇低鳴,提示該換電池。此為舉手之勞,但那裝置在天花板,要踩椅子登高作業。我提出給換電池,卻被兩位前輩同聲謝絕。
還有一次,淑平師母來電,她和余先生在《紐約時報》讀到閻連科的文章,讓我推薦幾本他的書。我將閻連科的《丁莊夢》捎給余先生和師母,又力薦《我與父輩》。閻連科筆下生息於中原的父老鄉親,精神血脈是中國鄉土原生文化的扭曲與延續。我特別關注書中農民命運所承載的文化符號,是受到余先生著作的影響,世間所有的故事與人,其實都有文化宿命之烙印。我說,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有我一位朋友,她家近傍余府,可請她借出此書給前輩送來。余先生當即謝絕,而且很鄭重地對我說,他不會“讓別人為我做任何事。”這就是余英時。
此前有一句話廣為流傳:“在沒有胡適的年代,我們有余英時。”現在沒有余英時的年代開始了,中華文化的託命者騎鶴西去,沒有余英時的年代何時才有大師降世?自陳寅恪之後,中華文明已在大陸注入另一河谷。沒有自由思想,就沒有余英時,他只能在另一片土地上開宗立說。
以我所了解的余先生和淑平師母,絡繹謁靈者驚擾余家陵墓,非他們所願。沒有余英時的年代,人們最好的紀念方式,是走進他開墾耕耘的田疇拾穗。桃李無言,下自成蹊,余英時不曾遠去。他走進歷史,擎起燭火,歷史樓閣的燈窗依次被點亮,那是思想之光。